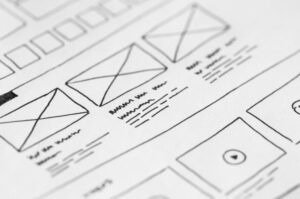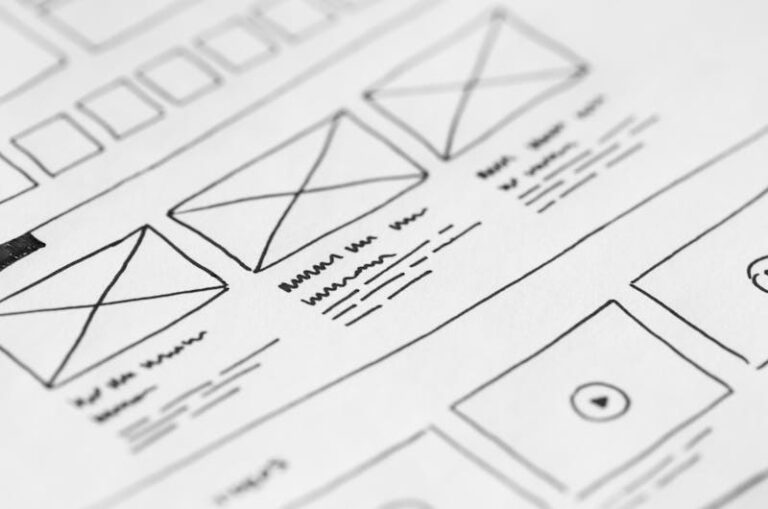佐佐木上班的地方是一個叫「高橋齒科」的矯齒診所,位於東京墨田區東墨田的一條斜街上。建築是一棟四層的舊樓,「高橋齒科」在三樓的東邊。診所不大也不算小,從門口進去,是接診檯和候診區,擺放着一排低矮的沙發。六個診室在狹窄的走廊上依次排開,佈局和造型怎麼看怎麼像一個公共廁所。佐佐木和老婆吵架時,一說:「我上班就夠累的了,你他媽還尋釁滋事!」老婆立即撇嘴道:「上班上班,不就是去個爛廁所嘛,有甚麼好牛逼的。」每逢此時,佐佐木雖然嘴上直罵「潑婦!」,但想起「高橋齒科」的佈局,心裡卻忍不住想笑,氣自然也就消了大半。
佐佐木是入了日本籍的華人,全名叫佐佐木真吾。十幾年前歸化入籍時,他在法務省提供的日本名姓備選表中,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名字。後來有人說:「這個名字也太日本了,完全是脫胎換骨啊。」佐佐木說:「脫胎個錘子!我老家是陝西一個叫柞木村的地方,這個名字的本意就是:我還是柞木的那個真我。」這樣的話佐佐木說了近二十年,但在他心裡湧上的,卻是越來越多的懷疑:我哪裡還是柞木的那個我?我都不知道到底甚麼是真我了。據說除神經細胞外,人體細胞更新週期為一百二十至二百天,佐佐木覺得自己來日本已經二十多年,細胞不知已經更新了多少遍,尤其在日本這樣異國他鄉,環境、食品、氣候等等,一切都與昔日大相徑庭,自己在肉體意義上應該說真的是早已經脫胎換骨了……為此,佐佐木總有一種「我既是我,又不是我」的糾結和困惑。
真吾的老婆名叫早紀,佐佐木的姓氏選定後,老婆自己選了這個名字。真吾當時問:「你為甚麼不選一個女人點的名字?早紀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嗎?」早紀說:「早紀早紀,就是讓自己早點長長記性。」真吾調侃地說了句:「那還不如叫早戒,早點把你的臭毛病都戒了。」抬眼卻看見了老婆的一臉怨氣,便沒敢再廢話……這一幕發生在十幾年前,因為是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所以佐佐木對所有細節總是記憶如新。那年老婆才三十來歲,還是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婦,無論是身段還是臉蛋,都相當耐看。甚至她嗔怒時瞪眼吊臉的模樣,現在想想都有些楚楚動人。
那是平成二十四年的事了,眼下已經是平成三十年的初春,距離平成時代的謝幕僅僅剩下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按說日本國改朝換代,對於佐佐木這樣一個歸化者而言,應該比四季的更替都無足輕重。但他內心卻總有一種人生逢變之感。儘管他並不清楚過了這個坎兒之後,生活到底是會柳暗花明,還是會雪上加霜。明仁天皇生前萌生退位之意,或許是因為年邁體衰而疲於國事,或許是不忍皇太子對皇位遙遙無期的等待,但不管出於何種考慮,都是父子之間、舊皇與新皇之間的一次平和交接,不會對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但佐佐木目前面臨的是一個真正的生活的坎兒,讓他對隱藏在其後個人生活的變化根本無從判斷。這個坎兒就是佐佐木早紀的最後通牒:要麼讓你女兒春香搬出去住,要麼我和兒子搬出去,咱們從此一拍兩散!
此話沒錯,春香是佐佐木與前妻的女兒,跟人家早紀確實沒有血緣關係。但早紀稱春香為「你的女兒」卻只是這幾年的事。她和佐佐木結婚時,被寄養在柞木村爺爺家的春香才三歲,她是和早紀一起被佐佐木接到日本來的。在春香成長的歲月裡,絕大多數時間都是早紀陪伴的。早紀當年曾動情地說:「比起她的親生父親來,我這個後媽才是她真正的親人。」事實上,童年時期的春香,與早紀的親密程度總讓不明真相的外人覺得,她是早紀的親生女兒,而佐佐木不過是她的繼父。春香十三歲那年,早紀生下了她和佐佐木的兒子秀忠。儘管早紀依舊疼愛春香,甚至因為怕被別人議論親疏之嫌而刻意偏愛春香,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佐佐木越來越明顯地感到,自己對春香的角色越來越回歸到生父,而早紀則越來越典型地成為了一個後媽。
星期五快到下班的時候,佐佐木又一次變得心神不安。他將此稱為「習慣性週末焦慮」,因為週末對別人或對自己的過去而言,是休閒放鬆和快樂愜意,而現在卻成了一種畏懼。平常上班,他以牙科診所加班的名義很晚回家,而在一家花店當合同工的早紀,每天上班又很早,所以夫妻二人一個戴月,一個披星,幾乎不用見面。而週末兩天,兩人都呆在家裡,就算分室而居,但住所就那麼大點面積,抬頭見臉,低頭聽聲,像兩隻關在籠子裡的老倉鼠,誰能躲得開誰的氣息?兩人的關係本來就已經一觸即發,而從小性格就一直古怪叛逆的春香無疑就是一個火柴匣子,稍不小心,隨時都有可能讓這個家玉石俱焚……
「唉!」佐佐木下意識地輕嘆了一聲。
「老師有心事啊!」正在收拾東西的護士清水開玩笑道,「最近不是總忘事,就是唉聲嘆氣的。事不能悶在心裡,應該找個年輕姑娘陪着喝幾杯。」
佐佐木說:「說話算數,走吧,我請你去喝一杯。」
清水快嘴快語地說:「老師就會拿老實人取樂。我這種人老珠黃的歐巴桑,哪裡還有男人捨得花錢請酒。再說了,一家人的晚飯還等着我做呢。」
看着清水扭着粗壯如桶的腰身從診室挑簾而出,佐佐木想起了她剛入職時青春少女妙曼的樣子。「也就不到二十年啊。」他自言自語地說。言畢卻疑惑起來:自己這是在為何而嘆?是為歲月催人老?還是為昨是今非?清水和妻子早紀年齡相仿,歲月摧毀了清水的身材,卻保留了她的性格中一如既往的寬容純良、樂觀豁達和善解人意。而這麼多年來,早紀的身材幾乎沒有發生甚麼變化,依然像少女時代一樣凸凹有致,所到之處還是會吸引男人們饞貓一樣的眼光。可歲月卻讓她的性格變得與昔日判若兩人,過去那個溫柔體貼、溫良賢慧的女人沒有了,代之而來的,是此刻正在家裡磨刀霍霍地等着與自己一決雌雄的那個悍婦……
想起早紀,佐佐木又嘆了口氣,然後磨磨蹭蹭地換好衣服,提着公事包下班了。出門後他到隔壁的便利店買了份三明治,邊往家走邊吃了下去。在日本很少有人在路上邊走邊吃東西。過去佐佐木挺在意入鄉隨俗的,但現在他不但甚麼都不在乎別人的眼光,有時甚至有與社會常理對着幹的故意。
佐佐木的家距離診所很近,坐車兩站,步行僅需一刻鐘。在日本就職以來,他從來沒有換過工作單位,但搬家的次數卻至少在六七次以上。開始時是租房住,由小到大,後來買了二手公寓,再後來買了新公寓,同樣由小到大,直到五年前才購買了眼下這幢一戶建。佐佐木對居住條件的改變沒有太大的感覺,他對頻頻搬家的感覺停留在距離概念上:那就是自己的住所離單位越來越近了。而這種越來越近的感覺,總讓他覺得自己像一隻風箏,而攥在早紀手中的那根看不見的線,收得越來越緊,自己越來越失去暢飛的自由,變得搖搖欲墜。
時值冬季,天氣陰沉,正薄霧般升起的暮色昭示着黑夜的到來。東京這座城市,對於佐佐木來說,其實是沒有冬天的。比起地處中國西北的故鄉,這裡永遠都是季節不甚分明的南方。佐佐木走得很慢。不時有路人從他身旁走過,有提着超市購物袋的主婦,有一邊嬉鬧一邊回家的孩子,有臉色陰沉的流浪漢,但更多的是三三兩兩的上班族們。他們一年四季都穿着廉價的西裝革履,手提公事包,正相約去某個居酒屋喝幾杯酒,以緩解一整天工作所帶來的壓抑。佐佐木甚至覺得,大多數日本上班族之所以能像一架沒有表情的機器一樣度過日日重複的一生,正是得益於下班後聚飲的有效調節和緩解。佐佐木能理解喝酒的樂趣,但他卻無緣享受。他是個滴酒不沾的男人。
在人們的概念中,滴酒不沾似乎是良好的生活習慣,但這個所謂的優點,對於佐佐木而言卻是一種天生的缺陷:因為不喝酒,他早已不在朋友聚會的名單之列。因為不喝酒,他經常遭到妻子早紀的抱怨:「一下班就回家的男人,在日本就意味着永遠沒有高升的機會,就注定是人生的失敗者。」這話很刺耳,但時間長了,佐佐木卻覺得不無道理。入職近二十年,他除了工資隨年齡而自然水漲船高之外,其餘一點變化都沒有。佐佐木滴酒不沾,並不像別人對酒精有過敏反應或其他身體原因,他完全是一種心理反應。
佐佐木的父親是個酒鬼,在他的記憶中,那個身兼村代銷店售貨員的西北農民,一年四季身上都散發着令人作嘔的濃烈的酒味。佐佐木的童年就是在酒鬼父親惹是生非的恐懼中度過的。在他小學二年級那年的夏天,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的父親大小便失禁,屎尿弄得滿牀都是,屋子裡惡臭沖天。母親在幫他收拾時忍不住責罵了幾句,結果卻招來醉鬼劈頭蓋臉一頓暴揍。母親被打得鼻青臉腫,還掉了兩顆門牙。
那天夜裡是佐佐木一生都無法忘記的噩夢。在父親痛毆母親的時候,他除了嚇得渾身瑟瑟發抖,內心更是充滿了無以名狀的仇恨。他幼小的心裡一直糾結着一個念頭,那就是要不要衝進廚房取來那把西瓜刀,狠狠地朝那個豬狗不如的男人的脖子上砍去。打完人的酒鬼又翻身睡去了。母親的反應讓佐佐木一頭霧水:她靜靜地坐在鏡子前,看着自己青腫的眼窩和流血的嘴巴,終年憂鬱的臉上竟然露出了一絲嫵媚的笑容。這讓佐佐木當時大惑不解,但第二天當他從夢中被人們慌亂的叫聲驚醒時,他就明白了母親昨天晚上的行為:夜裡,母親自殺了,她從後院那口深不見底的水井中一躍而下,輕鬆地結束了自己地獄般的生活……在佐佐木日後的成長過程中,酒一直就連同那個惡魔般的父親一道,成了他內心深處永遠無法抹去的陰影。
從明治大街走到向島警察署的十字路口,再向東一百米左右,在一個小巷子口左拐,就可以看見「河內屋」黃底黑字的巨大招牌。這是一家出售世界上各類大眾酒的連鎖店,因價格便宜而一直生意興隆。此時已經到了掌燈的時候,透過玻璃門,燈火通明的店裡依然有不少買酒的顧客。佐佐木那幢兩層的一戶建就在河內屋北面約三百米的地方,周圍除了兩家相距不遠的便利店,密密麻麻地分佈着新舊和佈局各不相同的一戶建。從這條小胡同一直往北走,就會有一條不寬的河流橫在眼前,那就是在史上曾多次泛濫成災的舊中川。佐佐木看了一眼,自己家一層和二層的燈光都亮着。這一般預示着妻子早紀和女兒春香都在家裡,因為如果只有早紀和兒子在家,勤儉持家的她是不會讓兩層的燈都開着的。佐佐木又下意識地輕輕嘆了口氣,覺得邁向家門的腿格外沉重。
「我回來了。」佐佐木打開門,一邊換拖鞋一邊說。這是日本人回家時習慣性的招呼用語,佐佐木入鄉隨俗地說了多少年了。可今天一說完,他卻悲從心來:你回來不回來的,又有誰會在乎呢?甚至不但不在乎,某人可能覺得你永遠不回來,死在外面才好。令佐佐木沒有想到的是,和自己冷戰、攤牌多日的早紀,竟一改平日裡視自己為空氣的做法,破天荒地從屋內迎了出來,對他說:「先去洗澡吧,飯已經做好了。」大概是覺得佐佐木的反應有些突然,早紀隨口又補了一句:「我有事給你說。」
佐佐木在洗澡的過程中,心裡一直忐忑不安。他猜不透妻子所說的「有事給你說」到底是甚麼事。早紀表情比平時輕鬆,似乎不像是甚麼壞事,可在這個家裡,能有甚麼好事呢?或許是一件對她而言利好、而對自己卻未必的事?是她主意已定要不惜一切代價離婚了嗎?或者是老買各種彩票的早紀中了大獎,忍不住要在自己面前瑟一下?……佐佐木胡思亂想,卻一無所獲。水從花灑裡像下雨般澆在身上,他卻忘記了自己是在洗澡,一直呆若木雞地站在那裡,直到兒子秀忠敲着浴室的門喊道:「爸爸,爸爸,沖個淋浴怎麼這麼長時間,媽媽讓你快點!」他這才從恍惚狀態中清醒了過來。
洗完澡出來,佐佐木看見今晚的餐桌十分豐盛。除了幾道早紀拿手的中國菜,最顯眼的是擺在中央的一道豪華刺身拼盤,一看就是從高級壽司店叫的外賣。
「是鴻門宴呢,還是最後的晚餐?」佐佐木坐下來,有些尷尬地開了句玩笑。
「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早紀一邊給三人面前擺放杯盤碗筷,一邊說,「就算咱們關係再爛,生活過得再水深火熱,今天這個日子總不能吃個三明治對付吧?」
佐佐木吃了一驚:早紀是我肚子裡的蛔蟲啊,她怎麼知道我剛吃了三明治?他疑惑地看着她:「今天甚麼日子?不就是個普通的週末嗎?」
兒子秀忠有些不耐煩地說:「是爸爸你的生日啊。我開始吃了。」然後就動起了筷子。
「對啊!我早忘了個精光。」佐佐木說。他是個在這方面特別糊塗的人,除了女兒春香的生日,別人誰的生日都記不住,包括父母和自己。事實上,他從小命苦,也就沒有生日的概念。和早紀結婚後,每年自己的生日都是在她的提醒和操持下,無論奢簡,總會作為一個紀念日度過。佐佐木心裡忽然湧上一絲溫暖的感覺,覺得最近自己對早紀的怨念有些太過陰暗了。
「咦,春香呢?我看見樓上的燈亮着。」佐佐木一邊說,一邊觀察着早紀的表情。儘管他唯恐這對已經變得勢如水火的母女出現在同一空間,但面對眼前一桌豐盛的家庭生日宴,如果他們夫妻加上親生兒子獨自享用,而將女兒獨自撇在一邊,他無論如何也是於心不忍的。
「剛才出門了,又忘了關燈。我喊她吃飯,人家連理都不理,真是養成仇人了。」早紀一臉怨氣地轉頭對秀忠說,「你上去把姐姐屋裡的燈關一下。」看着兒子一臉不情願的樣子,佐佐木馬上說:「孩子餓了,讓他吃飯,我去關。」然後立即起身去了樓上。
春香的房門緊閉着,要不是從外面看,根本不會注意到屋子裡的燈亮着。門上醒目地貼着一張表示拒絕的手的圖案,下面是一行血紅色的列印字體:未經允許,任何人不得入內!其中「任何人」三個字,是特意加大加粗的。佐佐木推開房門,眼前的情景讓他大吃一驚:這哪裡是一個少女的臥室,完全就是日本人所說的「ゴミ屋敷」(垃圾屋)!六疊的榻榻米上,到處雜亂地堆放着衣服、書籍、空的飲料瓶和各種各樣的日用品,睡墊上的牀單和被子堆成一團,屋角的一個穿衣鏡前,亂七八糟地擺滿了化妝品……
儘管早紀經常抱怨女兒把自己的屋子搞得像個豬窩,佐佐木還是沒有想到會糟糕到這樣令人目不忍睹的地步。佐佐木在伸手關燈的同時,一股怒火就莫名地躥上了心頭。但他卻不知道這無名之火該衝着誰發。早紀對春香的厭棄,除了無法明目張膽地偏向親生的秀忠之外,最大的矛盾就來自對這個叛逆少女生活習慣的不滿。佐佐木的怒火無法衝着女兒春香,是因為女兒毫無秩序的生活習慣其實只是一種故意,是對早紀井井有條、乾淨整潔的生活秩序的挑戰,起因依舊在妻子那裡。但他也無法抱怨早紀,因為不是她不去收拾,而是因為屋門上「未經允許,任何人不得入內!」的警示招牌,這是早紀回擊自己的最好理由。事實上,早紀曾有幾次自作主張地替春香把房間收拾得利利索索,但換來的不但是春香一臉怒氣的抱怨,而且她讓繼母忙了大半天的成果瞬間又恢復成了原樣。「唉!」佐佐木嘆口氣走下樓去。他知道自己的怒火除了變成滿腹的無奈,就是對自己失敗人生的無力自嘲。
好久沒有這樣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飯了。但即便是自己的生日,佐佐木也沒有一絲快樂的感受。早紀給自己倒了杯葡萄酒,給丈夫和兒子各倒了杯果汁,端起來用日語說:「生日快樂!」佐佐木碰了一下杯,卻用中文說:「有甚麼好快樂的?過一次生日,離死近一步。你先把要說的事說了,我急脾氣,否則吃不下飯。」早紀卻賣關子地說:「先告訴你是好事,你猜是甚麼事。」佐佐木心想:好事也是你自己的好事,這個家裡已經不可能有對大家都好的事了。還不等他說話,早紀又像他肚子裡的蛔蟲一般地說:「對每個人來說,這都是一樁好事。」佐佐木說:「你終於狠下心來要離婚了?果然是鴻門宴啊。」不料早紀說出來的事讓佐佐木大吃一驚:就在今天下午,春香對她說,下週要搬出去自己住了。佐佐木剛一聽完,就立即炸了窩:「你他媽的終於孤注一擲了!她一個無業遊民,怎麼去外面住?哪兒來的房租錢?告訴你,你這麼容不下一個孩子,要走也是你走!」
兒子秀忠看到父親吹鬍子瞪眼的樣子,飛快地扒完碗裡的飯,一臉驚恐地回自己的屋裡去了。佐佐木心想,既然你敢毫無顧忌地觸碰老子的底線,那也只好魚死網破了。但早紀一反平日裡睚眥必報的常態,不但沒有動怒,反而笑了起來:「還沒弄清楚就開始冤枉人。私下嘮叨歸嘮叨,但我從來沒有在女兒面前提過半句,要搬出去住是她自己的主意。」佐佐木憤然道:「扯淡!你以為我真傻啊。」……但一場看似不可避免的家庭風暴,卻最終還是被早紀運籌帷幄地化作了輕風細雨。據早紀說,這個決定是今天在母女間沒有任何衝突的情況下,春香主動說出來的,就連她自己也感到意外和吃驚。
「怎麼可能?就她在小飯館打工那點收入,連零花都不夠,還租房?如果不是家裡待不下去,她會冒出這樣絕望的想法?」
「這話沒錯,她怕真是在這個家裡待不下去了。」早紀的口吻聽上去有些陰陽怪氣。
「你甚麼意思?難道責任在我?」佐佐木說,「別忘了,我可是她親爹。」
但早紀接下來說出的話,卻讓佐佐木大吃一驚:春香之所以在家裡待不下去,是因為她懷孕了!這是一個讓佐佐木感到五雷轟頂的消息,這樣的事他甚至想都沒有想過。看着佐佐木一臉懵逼的樣子,早紀不以為然地說:「別搞得像天塌了似的。春香前年就已是成人,懷孕也是人家的權利。」
佐佐木想說「你他媽放屁!她要是你的親生女兒,你會這樣站着說話不腰疼嗎?」但話到嘴邊卻被他嚥了回去,而是狐疑地問:「你怎麼知道的?確定嗎?」
「她的肚子都隆起來了。開始我還有點納悶,但昨天我在衛生間的垃圾桶裡,發現了一根用過的試孕棒,才恍然大悟。要不是這檔事,她今天怎麼會突然說起要搬出去住。」
「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誰嗎?」沉默了半天,佐佐木才猛地想到了這件事上。
「我哪裡知道,她跟我搞得跟仇人似的,這樣的事怎麼可能對我說。」早紀邊說,又邊給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
佐佐木看着早紀喝酒時享受的表情,恨不得奪過杯子猛地潑在她的臉上。但理性告訴他不能這樣意氣用事。叛逆的女兒從小就跟自己非常疏遠,懷孕這類女人的事,雖然早紀與春香間矛盾不斷,但最終還得由這個後媽出面才能解決。佐佐木嘆息了一聲,抱怨道:「出了這麼大的亂子,你居然說是好事,你是怕人不說後媽歹毒啊。」
早紀把一個金槍魚壽司放進嘴裡,一邊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邊說:「後媽要都當成我這樣,竇娥還有甚麼資格喊冤?我說這是件好事,你以為是在幸災樂禍呀?你耐心聽我說完,就明白一個當媽的良苦用心了。」佐佐木哼了一聲沒有說話,他心想:就算你有把死人從棺材裡說得坐起來的口才,也不可能把這樁讓人心煩的亂子說成天掉餡餅的好事吧。
早紀今天的情緒很好,她吃喝說話兩不誤地對眼下佐佐木家庭局勢做了精辟的分析:脾氣古怪、性格叛逆的女兒春香大學畢業已經一年,卻不去正式就職,除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打點零工,整天就是瞎混日子。從試孕棒來看,懷孕對她也屬於意外。但懷孕後她沒有偷偷去墮胎,而是選擇離家生活,說明對象是個負責任的男人,兩人極有可能打算要這個孩子。這樣的話,他們結婚就勢在必行。而有了小家庭,對春香而言絕對是好事,這不但能改變她現在這種渾渾噩噩的生活狀態,而且會擁有一份真正的快樂和幸福。春香的問題解決了,對你對我,對這個家庭,豈不都是好事?
「等她搬走後,我把那間屋子好好整理一下,作為你的書房兼客房。沒有了垃圾屋,我的整個心情都不一樣了。」早紀憧憬着即將到來的清靜生活,興致勃勃地說。
「我們當父母的,總不能連對方是誰,是幹甚麼的,他們兩人到底對以後的生活作何打算都不知道,就稀里糊塗地將女兒放任自流吧?」佐佐木說。
「你又不是不知道春香的脾性,我可以旁敲側擊地問問,但她要是不願意說,咱們又能怎麼辦?對方是誰你左右得了嗎?都甚麼時代了,而且這是在東京,而不是你們陝西鄉下,春香已經是成人,她就算找個老頭子,你能有權干涉咋的?」
「八嘎!」佐佐木突然憤憤地冒出來一句髒話。他不知道是在罵誰,是那個尚不知道的神秘男人,是不省心的女兒,是自私偏心的妻子,還是把生活過得一地雞毛的自己。對於早紀的話,他既不甘心就此認同,卻又找不出反駁的理由。早紀今天對自己的態度一反常態地寬容,但剛進家門時泛起的那絲溫暖感此刻也變成了憤怒。剛成年的女兒不明不白地懷孕了,你一個當母親的竟然不知道懷的是誰的孩子!但佐佐木心裡明白,更應該承受這種指責的是自己。早紀畢竟是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而自己作為她的親生父親,在孩子成長的漫長歲月裡,又操過幾分錢的心?
佐佐木身心疲倦地對早紀說,「你抽空還是和孩子推心置腹地聊聊,這種事,我一個當爹的,沒法開口。再說了,她自打來日本,甚麼事都是跟你商量,我跟她說甚麼都愛搭理不搭理的。」他長嘆一聲,將杯中剩餘的果汁一口喝乾,自嘲地道:「大禮,大禮啊,這真是送給老子生日的一份大禮。」
週末兩天,佐佐木一直忐忑不安。他似乎既盼着見到女兒,又害怕見到。春香懷孕的事是妻子意外得知的,儘管他讓早紀找個合適的時間好好和女兒談談,但其實他也不知道這張紙捅破了到底會有甚麼結果。但週末兩天春香一直沒有回家。從中學時代開始,春香就有夜不歸宿的記錄。但那時只是偶爾為之,而且去哪個閨密家都會告知早紀。但隨着母女關係的惡化和自己年齡的增長,她夜不歸宿的次數越來越多,而且對父母的詢問總是大為光火。而在她成年之後,春香覺得父母過問的資格已經徹底喪失了。週日晚上,佐佐木若有所失地不斷樓上樓下來回走動。他聽見分居後一直住在兒子臥室裡的早紀發出的鼾聲,覺得內心的厭惡更是變成了一種隱隱的仇恨。到十二點的時候,他在春香虛掩的房門前發出輕輕的一聲嘆息,悻悻地下樓去了臥室。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佐佐木在上班的時間裡總有些情緒恍惚。做牙醫十幾年,他居然像個剛入職的新手一樣,一會兒忘了戴手套,一會兒拿錯了磨牙鉗,甚至有一次差點拔錯了一個年輕患者的病牙……護士清水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她憂心忡忡地對佐佐木說:「老師還是有心事啊,而且最近變得越來越重了。」日本同事其實很少說這些可能牽扯到別人隱私的話,但佐佐木明白清水這個善良的女人是真的關心自己。他苦笑了一下說:「我能有甚麼心事,大概只是過早地進入老年癡呆期了。」這段時間裡,春香一直沒有回家。佐佐木給這個自從來日本就一直跟自己非常疏遠的叛逆女兒發過幾回短信,也只是故作歲月靜好地表達了作為一個父親的關懷,甚麼多餘的廢話也沒敢多說,但依然像往常一樣泥牛入海,沒有得到半句回覆。
妻子早紀對佐佐木的態度卻明顯變得溫和起來。她那張本來吊得越來越長的臉開始回彈,竟漸漸讓佐佐木有了歲月倒流的錯覺。早紀對兒子秀忠耐心、平靜和充滿母愛的樣子,讓他想起了當初三口之家曾經和諧和讓人懷念的往昔。但這種懷念是短暫的,它瞬間就會被缺憾、失落和忿忿不平所取代。讓佐佐木吃驚的是,這種情緒不僅針對妻子早紀,甚至更針對兒子秀忠!
其實佐佐木知道自己的所謂吃驚,不過是理性對自己長期以來一種陰暗心理下意識的掩飾。自己對兒子秀忠從出生開始,就帶有一絲敵意。仔細想來,這種敵意與自己的酒鬼父親有關。佐佐木的父親就是在兒子秀忠出生那年死去的。母親的自殺,讓當時尚年幼的佐佐木對父親的仇恨變得不共戴天。他當時盼望長大的唯一心願,就是有足夠的力氣殺死父親,給可憐的母親復仇。但代替了母親角色的姐姐,卻用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慢功夫,讓他復仇的動力在後來的歲月中變得越來越微弱。等他有足夠的力量殺死酒鬼的時候,這種心思卻一點都沒有了。但他的厭惡感始終沒有消失過,他希望父親趕緊死去,以一種起碼大於母親痛苦的方式死去。他曾設想過父親的許多種死法,因惹事生非被人砍死,醉臥街頭被車撞死,失足墜崖而屍首不全,口生惡瘡而無法進食……佐佐木最怕父親在一場酣醉之後再也沒有醒來,如果那樣,就太便宜這個禍害別人一生的畜生了。
但事情的結局卻偏偏難遂人願,就在秀忠出生的當天晚上,姐姐給佐佐木打來了越洋電話:父親死了,三代單傳的父親在得知自己有了大胖孫子之後,從下午開始就狂飲慶祝,任姐姐怎麼勸也勸不住。醉酒後的父親順勢在炕桌旁倒頭睡去,等姐姐做好晚飯端上桌時,才發現他已經駕鶴西行了。姐姐在電話裡說:「爸是含笑走的,而且那麼大歲數,在柞木村也算是數一數二的高壽老人,你不要太傷心啊。」大概從這個電話開始,佐佐木就對兒子秀忠產生了一種難以說清的複雜情緒。
酒鬼父親含笑而終,是對佐佐木人生信念赤裸裸的嘲弄。佐佐木回想自己的成長經歷,雖然幾乎所有的選擇,都是為了對抗父親,但結果卻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因為父親不喜歡,他賭氣和當時只是一個普通朋友的前妻結婚,但最終的結局卻是離異;父親一心想要個孫子,佐佐木發誓不讓他這種愚蠢的願望得逞,但秀忠的出生卻還是遂了酒鬼的念想;即便因為反感父親而對酒的厭惡,也給自己的人生造成了莫大的困惑……佐佐木有時覺得,即便父親已經死去多年,即便自己已逃到了遙遠的異國他鄉,但他的陰影卻依然籠罩着自己的生活。
週四下午,佐佐木正在上班,接診護士卻急匆匆地跑到他的診室說:「佐佐木老師,電話!您夫人的,說給您打手機無數次都沒人接。」佐佐木一邊往接診檯走,一邊尋思:早紀能打工作電話找自己,肯定是出了甚麼亂子!可會是甚麼亂子呢?各種念頭在他的腦海裡急速地浮上,又被一一否定,在這個家裡,唯一可能出下亂子的,似乎只會是女兒春香……結果他剛拿起電話,話筒那頭就傳來了早紀慌亂而驚恐的聲音:「你趕緊來中村病院急救科,我快要崩潰了。」佐佐木嚇得渾身一激靈:「病院?出甚麼事了?」此刻他唯一的猜測,是女兒無法承受意外懷孕的壓力而選擇了輕生。不料早紀在電話裡哭了起來:「秀忠放學的路上出了車禍,你趕緊過來。」
在趕往中村病院的出租車上,佐佐木的手一直哆嗦個不停。這是他特有的一種古怪的強迫性反應。此症起於母親自殺後不久。嗜酒如命的父親缺酒時,雙手抖動得連帽子都戴不到頭上。每逢此時,他便像瘋了一樣逼着姐姐或自己去小店賒酒,非打即罵。父親痛苦的咆哮聲,像冬天村外荒原上恐怖的狼嚎。從那以後,每逢聞見酒味,佐佐木的手就會像父親一樣不由自主地哆嗦起來。此症無藥可救,發展到後來,無論遭遇任何驚慌之事,都會觸發佐佐木這種強迫性反應。
「唉!」佐佐木忍不住又輕嘆了一聲。他固然對秀忠忽遭意外感到憂慮,但引發他強烈反應的,卻是他對自己這種憂慮出於理性而非自然反應的驚慌:從早紀嘴中聽到出事的是秀忠而非春香時,那一刻泛上他心頭的,居然不是意外和震驚,而是一種類似如釋重負的感覺。出租車在明治大道上飛快地一路向西,兩旁熟悉的建築卻呈現出一種不真實的陌生。「你這個混蛋,這對一個無辜的孩子是不公平的。」佐佐木在心裡暗暗地罵着自己,手不由自主地哆嗦得更加厲害起來。
佐佐木到達中村病院的時候,早紀正像頭被圈在籠中的狼一樣,在醫院大廳裡來回走動。佐佐木問:「兒子呢?到底怎麼回事?」早紀帶着哭腔說:「進手術室了。我也是接到老師電話才知道的,說是在便利店門口被一輛自行車撞倒了。」佐佐木說:「自行車啊?那不應該有太大的事。」早紀一聽便怒形於色地道:「被自行車撞死的也不在少數。要不嚴重,能進手術室嗎?你倒是心大,就好像兒子不是你親生的。」佐佐木怔了一下,嘟囔道:「我這不是為了安慰你嘛,怎麼搞得好像我是肇事者似的。」
佐佐木詢問了救急室的接診護士,說是兒子倒地時磕到了頭部,具體情況要問大夫才能知道。在等待手術結果的過程中,夫妻倆一直坐在走廊的一個排椅上,各懷心事,彼此沉默。令佐佐木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內心並沒有作為一個親生父親應有的焦慮和不安,而是想起了前妻在生春香時難產的事。
那時他大學畢業不久,月收入不過幾十元。姐姐給父親打了電話,父親極不情願地送錢到縣醫院時,居然背地裡嘟囔了一句:「媽的!生個不帶把的,還用得着這麼費勁。」想起這件事,佐佐木覺得內心一陣痙攣。在漫長的歲月中,他與酒鬼父親貌似的和解如同剛被修補如初的瓷器一樣再次變成碎片,怨恨依舊新鮮如剛剛割裂的傷口。他設想着父親如果在世,自己把他三代單傳的孫子此刻正生死未卜地躺在手術檯上的消息告訴他時,老酒鬼會有怎樣的反應?這個想法讓佐佐木忘記了對秀忠手術的擔憂,甚至心中泛起一絲模糊的快感……一旁早紀忍不住的暗泣聲,讓佐佐木從幻想中驚醒過來。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手不知何時已經恢復了正常,一點哆嗦的迹象都沒有了。
一種從未間斷過的失敗感襲過佐佐木的全身。他覺得自己的人生比酒鬼父親還要失敗,父親儘管給家人帶來了無盡的痛苦,本人卻享受了自私但自由的快樂。而自己呢,既沒有給家人帶來快樂,也永遠活在無盡的痛苦之中。想着從出生時就被厭棄的女兒,想着自己對兒子因為對抗父親而不公平的漠然,想着這個在異國他鄉正走向分崩離析的家,佐佐木不知不覺間流下了一行淚水……
猶豫良久,他給女兒春香發去了一條短信:弟弟出了車禍,你甚麼時候能回家看看嗎?